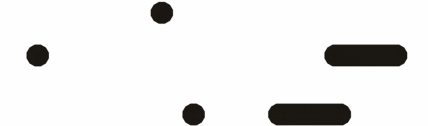Oscar Murillo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当代艺术家,以其富有创造性和流动性的艺术实践闻名。2018年11月10日下午,Oscar Murillo 与 Victor Wang 在油罐艺术中心进行对谈,与观众分享他的艺术创作。
讲座内容精选
Victor:Oscar让我意识到,对于很多的艺术家,我们会最先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地点、所住城市,而Oscar 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会去很多不同的城市,好像他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状态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艺术家与其工作地点的联系,以及相应的归属感。
Oscar:我现在给大家呈现的是2015年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是我2014年开始创作的。这是一件与他人合作的作品,其中包含我对绘画的思考、对作者身份的思考。这件作品呈现的是一个负面的环境,想要表达的是去除国籍、反乌托邦、去除层级。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场馆里,我们看到有英国馆、法国馆等不同的场馆,是一个层级非常森严的体制。刚才Victor也提到,一个艺术家有多个不同的工作地点,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光鲜的一件事情,但其实不然,这反而是一种无国籍的状态。
Victor:我知道你会在跨国旅行过程中,在飞机、火车上画画。这种做法非常有意思,因为在飞行过程中,你不是在地面,而是在空中,而且是在非常高速的行进状态中创作。在这样的状态中,地域的概念似乎模糊了,而且又不是在传统意义上艺术家的工作室空间中创作。
Oscar:的确,一开始是一种非正式的形式,在飞行途中进行绘画创作,是一直在持续行进过程中的一种连续创作状态,消除了对地理、地点的感觉和概念。相信在座各位都有长途飞行的经历,特别是这个行业中的策展人、艺术家。我在过去的四年中一直尝试在飞机的客舱空间中进行创作,一开始是非正式地创作,后来转变为不断地有成果的输出,这也是为后续更为正式、大型的创作打下基础。
Victor:这种创作实践是在移动的工作室中,打破了原来在传统工作室中、跟地点有关的创作行为实践。这颠覆了认为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就应该代表某个国家、地区、艺术家身份的传统西方观点。这是后工作室时代的创作。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俯瞰地面,地面的界限就显得非常遥远。
Oscar:我想谈一下我在家乡哥伦比亚的第二次展览。能够在我的家乡哥伦比亚展出,给了我一个背景,去理解我为什么会创作出我所创作的作品。
就像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是在我家乡的一个糖厂,我邀请了十几名工人一起到纽约进行展出。这家糖厂一百年前是与剥削和奴隶有关联的。与此同时,糖厂的员工又是同一个社区里的。这让我联想到,这家糖厂的命运与美国中西部过去30多年来制造业的衰落十分相似。在全球化的贸易浪潮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地区,贸易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大家常常讲的人工智能,未来很有可能取代人类的劳动。同时,这个展览又是在全球的经济中心,纽约市市中心David Zwirner这样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画廊中展出,让人联想到权力、资本主义。
当我回到哥伦比亚,作为一个当地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与工人阶级、工薪阶层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把这样一个半自传性的项目放到纽约,在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商业化的画廊中进行展出。这个项目可以从多个角度看,核心不一定是一种抵抗,而是对家园的赞美和庆祝。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着不同阶层体系,看到糖厂员工的社区和生活方式,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从个人角度而言,可以说我是在反观博格达的这群工人,对他们的生命流逝进行持续的默哀——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跟机器打交道。这座工厂本身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那么,我在香港刚结束的新展览和五年前这场在纽约的展览之间又有何联系?看上去有某种社会、政治方面的联系,可能也有美学上的联系。我一直在纠结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到底要不要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我的态度是,不应该从道德的出发点进行创作。
尽管作品的主题可以是贸易、全球化或是不同的阶级,但是我的创作欲望最初并不是因道德而激发的。当然艺术可以有政治含义,可以从政治、社会、审美等多个角度出发,但我更享受的是从美学的角度,去看不同作品的形式、色彩,欣赏和享受艺术创作的过程。两方面看似是矛盾的,但实际是可以共存的。像上海双年展中很多作品都会经过官方的审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古巴,这反而也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观众提问精选
观众:您一直在行进中的创作状态,这是不是一种道德的生活和创作的状态?比如说,对于环境而言?您能够这样做,是否因为您拥有某种特权?艺术家是否应该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创作?
Oscar:确实,一直在行进过程中创作是不道德的,因为这对于环境不好,对于我自己的健康也不好。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做,所以这象征着我的某种特权。从这个角度,我无法为自己的做法辩解。艺术家作为一个在全球迁徙、不断移动的背包客,游走四方,这样做的道德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出生的环境是非常民族主义的,信仰体系中有很深刻的民族主义的偏见。艺术家以艺术为工具,通过不断的旅行获得新的知识。委内瑞拉、伊拉克、叙利亚、中东有很多游离失所的难民涌向欧洲,只要去英国的南部边境就能看到这样非常严重的现象。我亲历了冲突,作为一个目击者,见证了这样的过程。我能体会到人们游离失所的状态,体会到迁徙对于环境、水、岛屿的影响。